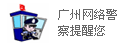塵肺病人的春天何時才能降臨
“我就只想再活二年。我兒子今年24歲上大三,明年就畢業(yè)了。我想看著他畢業(yè),看著他結(jié)婚成個家。”說起心愛的兒子,郭海良眼淚順著眼角流到了枕頭上。
“就是給我一百萬,我也再不會去挖煤了。多少錢也換不回我的命啊!”
可是,現(xiàn)在后悔的郭海良在知道得了塵肺病之后依然堅持打巖石。事實上,他是房山區(qū)關(guān)停小煤窯政策出臺后,最后一個離開他所在的榮耀礦的。
“我希望自己得癌癥”
郭海良在去年6月被北京市朝陽醫(yī)院確診罹患塵肺三期。此后他回到了位于河北省圍場縣郭家灣鄉(xiāng)榆林樹村的家中。

郭海良右側(cè)臥躺在土炕上,身上蓋著一件棉服。兩個耳朵上掛著根管子,用來給鼻孔不斷輸送氧氣。右胳膊扎著輸液的針,輸液的瓶子掛在穿過煙囪的一根繩上。
他已經(jīng)在家里的土炕上躺了兩個多月。這段時間,他無法站立、無法直接呼吸,必須24小時吸氧、24小時不停注射葡萄糖和消炎藥的混合液。
因為左肺已完全“硬邦邦”的,郭海良無法向左側(cè)臥,否則會疼痛難忍。他的右肺也只剩三分之一勉強發(fā)揮著功能。
3月4日,郭海良的堂弟到圍場縣醫(yī)院替他拿CT片,醫(yī)生說,他的肺功能正在完全喪失,現(xiàn)在能做的就是開點藥維持生命,“他的日子不多了,可能也就一兩個月”。
這些話,堂弟沒告訴郭海良夫婦。
郭海良似乎也感覺到了什么,他在上周主動給北京市義聯(lián)中心的韓世春律師打電話,想請他幫忙,希望有人能救自己。
“我就只想再活二年。我兒子今年24歲上大三,明年就畢業(yè)了。我想看著他畢業(yè),看著他結(jié)婚成個家。”說起心愛的兒子,郭海良眼淚順著眼角流到了枕頭上。
喘著拉風(fēng)箱般的粗氣,伴隨制氧機嗡嗡的馬達(dá)聲,房間里響著奇怪的聲音。郭海良說,他現(xiàn)在希望自己得癌癥。“得了癌,我可以把那個地方拉掉。得了這病,我拉不掉啊,太憋得慌。”
郭海良知道,得了這個病最后只有一種結(jié)果——憋死。
“死的時候,頭會憋這么大。”郭海良用手比劃出兩個頭大小。
這樣的事情也發(fā)生在了郭海良同鄉(xiāng)人的身上。
去年,一個三十五歲的年輕人,不知從哪里挖煤染病回到郭家灣鄉(xiāng),因為什么都不懂,沒有獲得一分錢賠償,病情重又無錢醫(yī)治,他選擇了自殺。
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,年輕人堅持要到門外透氣。家人以為他好些了,把他扶到門口的墻邊讓他獨自曬太陽。
花了4個小時,走了50米,年輕人一頭扎進(jìn)了家門前的河里。
等家人把他救上來,人已奄奄一息。
年輕人最終離開了人世……
這樣的事讓郭海良對自己的生命充滿了矛盾。
郭海良哭著說自己想多活兩年,能看到兒子自立。可有時候他又覺得喘氣實在困難,巴不得一下死了痛快。
病急亂投醫(yī),郭海良希望洗肺能夠救命。兒子幫他從網(wǎng)上查到了專治塵肺病的北戴河療養(yǎng)院熱線電話。郭海良試著打過幾次。
那頭接電話的醫(yī)生每次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他洗肺的要求。“聽你這聲音我就能判斷,你不能洗肺了。騙你來,不是讓你白花錢嗎?”
“多少錢也換不回我的命啊”
郭海良所在的村莊是個貧窮的地方:沒有任何礦產(chǎn)資源,十年就有九年旱。不到十年時間,村里從六十戶人家減少到二十戶,很多人出去打工再也沒有回來。村莊和土地逐漸荒蕪,山上的野兔和野雞卻重新回來了。
在出門打工之前,郭海良靠種四畝玉米地為生,一年累到頭只能掙兩千塊錢。
2006年,眼見著上高中的兒子花銷越來越大,郭海良感到手頭越來越緊。
這年的10月,聽別人說到煤礦挖煤來錢快,從未出過遠(yuǎn)門的郭海良毫不猶豫地選擇抓住這個“好”機會,到了北京市房山區(qū)的榮耀礦。
為了比普通挖煤的每月多掙一千塊錢,郭海良干起了打巖石的活。
與挖煤相比,打巖石的工作環(huán)境更惡劣,粉塵更多。一些老礦工知道這一工種的危害,要么不愿意干,要么干一兩年就轉(zhuǎn)換工種。老實巴交的郭海良不知道其中厲害,從進(jìn)了煤礦到最后離開,他打了近四年的巖石。
郭海良本來有機會早點明白工作的危害有多大,可是他錯過了。
他所在的小煤礦曾一度沒有機械運煤裝置,從井下挖出來的煤,是靠工人驅(qū)趕一頭驢繞動杠桿,像打水那樣將煤拉到地面。
那頭驢干了不到三年的活,腳步卻越來越慢。有一天它站著不動,工人狠狠地抽動手中的鞭子。驢沒動,轟然倒下。
驢再也沒睜開眼睛。礦工們見驢死了,都合計著吃驢肉。大家動手切驢,切著切著刀卻碰到了硬邦邦的東西。打開驢肚子一看,驢的肺成了黑黑的石頭狀。
包括郭海良在內(nèi)的礦工都覺得這事奇怪,卻并沒往心里去。
直到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肺也慢慢變成了石頭,郭海良才發(fā)現(xiàn),他的情況其實和驢一樣。更糟糕的是,驢只是在井口拉煤都成了那樣,自己周圍的灰塵多出驢不知幾倍。郭海良不愿再往下想。
“如果能讓你重新選擇,還會去挖煤嗎?”
“就是給我一百萬,我也再不會去挖煤了。多少錢也換不回我的命啊!”
可是,現(xiàn)在后悔的郭海良在知道得了塵肺病之后依然堅持打巖石。事實上,他是房山區(qū)關(guān)停小煤窯政策出臺后,最后一個離開他所在的榮耀礦的。
從住的工棚到煤礦,天天都要爬同樣的坡。但郭海良發(fā)現(xiàn)“坡越來越長,爬起來越來越費勁。”盡管干活已經(jīng)開始?xì)獯廊粓猿帧?ldquo;實實在在說,沒想到身體會這么快就不行了,那時候堅持干活還是為了掙錢。”
給醫(yī)院的錢像“流水”一樣
在煤礦干了不到六年,郭海良掙了20多萬元,養(yǎng)活了自己和老婆,還供惟一的兒子上了西安的大學(xué)。去年11月,在北京市有關(guān)部門的協(xié)調(diào)下,郭海良與別的患病工友一起拿到了賠償金。
拿著17萬塊錢,郭海良以為這筆錢能夠堵上以前治病的“錢窟窿”,還能留下不少繼續(xù)治療。
然而,郭海良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了起來,每天付給醫(yī)院的錢“像流水”一樣,“一天就要花三四百,到三月份,已經(jīng)花了二十六七萬。”郭海良的妻子劉金榮說,賠償金早花完了,現(xiàn)在的醫(yī)藥費都是親戚們東挪西湊來的。
如果不是郭海良突然憋得昏死過去,家人已經(jīng)不敢輕易送他進(jìn)醫(yī)院。“上次他才在醫(yī)院住了不到10天,就花了三千八。”
從2月下旬到3月23日,郭海良已經(jīng)昏迷過四次。
“憋過去”的頻率越來越高,郭海良感到自己的情況越來越危險,求生的欲望讓他掙扎著給北戴河療養(yǎng)院一次又一次打去電話,也給曾經(jīng)幫助他討到補償金的韓世春律師打電話。
郭海良只是希望律師能救救他。他不斷喘著氣說,這么嚴(yán)重的情況,沒有醫(yī)療報銷,一次性給他17萬元賠償金根本不夠醫(yī)藥支出。
在聽說有的工友沒有選擇一次性賠付而是按月領(lǐng)取的辦法,還可以享受醫(yī)藥費報銷待遇后,郭海良特別后悔當(dāng)初沒有多了解情況。他委托韓律師給自己打官司,希望能“反悔”,選擇按月領(lǐng)取賠償金同時享受醫(yī)藥費報銷的工傷保險待遇。
郭海良對韓世春說:“謝謝你幫助我,如果需要我出庭,我就是掛著氧氣也要去。”
在郭海良家的廚房里,放著兩大盆有些發(fā)黑的咸菜疙瘩,櫥柜上放著幾個土豆、兩包平菇和一包豆芽。
劉金榮說,平時他們就吃咸菜、土豆,有游商來的時候才能買點別的菜。但是,肉是買不起的。
郭海良家實在太窮了,可比貧窮更嚴(yán)峻的,是郭海良的生命正在快速凋零。
但盡管如此,對于能否幫他打贏這個官司,義聯(lián)中心主任黃樂平律師卻并不樂觀。
離開郭海良的家已是黃昏時分,劉金榮開始燒火、做飯、熱炕。
濃煙在不大的幾間屋子亂竄,讓人難以呼吸。因為房子的男主人無力整修煙道,爐灶和土炕的煙道也形成了惡性循環(huán):煙道被煤灰堵住,灶里產(chǎn)生的煙排不出去,只能憋在屋里,就像它們男主人的肺……
郭海良們的春天何時來到 ?
從北京義聯(lián)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得到消息,一位三期塵肺病人向他們尋求法律援助,而且患者可能時日不多。
此前我曾多次采訪過職業(yè)病患者,但情況如此嚴(yán)重的,還是第一次碰到。
3月23日早晨6點30分,跟隨義聯(lián)的公益律師團(tuán)隊從北京出發(fā),開了七個小時的車,一路溝溝坎坎彎彎繞繞,到了郭海良貧窮的家。
一套三個房間的平房,進(jìn)門那間既是門廳又是廚房。門廳左右各一間房,大點的那間不到10平方米,是郭海良夫婦的臥室。臥室內(nèi)除了一臺電視外,再沒了別的電器。墻是用紙糊的,炕沿已經(jīng)因為使用日久,變得黑而亮。門廳左邊的房子,被用來儲物,地上放著兩大筐咸菜疙瘩,一口水缸、一個老舊的小櫥柜。
到了郭家,難免會想起一個詞——“家徒四壁”。
如果不是跨進(jìn)了郭海良的臥室,我從來不知道人的呼吸聲音會如此巨大。聽著他困難地喘氣,我自己也感到一陣陣胸悶。
一個今年剛46歲的男人,本來正是黃金年齡,不僅是干活的好手,更是家里的頂梁柱。現(xiàn)在卻躺在床上,一切動作、一切生活都必須依靠家人的幫助。
說起兒子,說起心中的愿望,郭海良喘著氣、眼淚順著臉淌了下來,他側(cè)了一下頭,想悄悄地把眼淚蹭在枕巾上,他連擦臉都做不到了。
郭海良明白,得了塵肺病,只有一個死。但他還是希望能通過各種治療多活兩年。因為他放不下心愛的兒子。
每天巨額的藥費無法報銷,讓郭海良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現(xiàn)在他們面臨的經(jīng)濟問題本可以通過按月領(lǐng)取賠償金的制度來避免。
早在2004年,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出臺文件對農(nóng)民工參加工傷保險予以規(guī)范——1至4級傷殘長期待遇的支付,可試行一次性支付和長期支付兩種方式,供農(nóng)民工選擇。在農(nóng)民工選擇一次性或長期支付方式時,支付其工傷保險待遇的社會保險經(jīng)辦機構(gòu)應(yīng)向其說明情況。
郭海良的三期塵肺正屬于1至4級傷殘。但郭海良說“不知道有這樣的規(guī)定”,他更不知道自己本來擁有選擇權(quán)。
事實上,除了郭海良,還有很多職業(yè)病患者正在遭遇這樣的境況。
在今年兩會前,義聯(lián)中心發(fā)布了對罹患職業(yè)病患者的一項調(diào)查,結(jié)果顯示——獲得一次性賠償?shù)模骄咳祟I(lǐng)取到的賠償僅90742元。領(lǐng)取了一次性賠償?shù)幕颊咧?8%表示這些賠償無法保障其后續(xù)的醫(yī)療和生活,47.5%表示這些賠償最多只能維持2年以內(nèi)的醫(yī)療和生活。
一個喜訊是,職業(yè)病防治法已經(jīng)列入今年的立法規(guī)劃,這些現(xiàn)實問題有望通過立法獲得“糾正”。但郭海良說他不知道什么是職業(yè)病防治法,更不知道這個法律的修改與他有什么關(guān)系。
已然走到生命盡頭的郭海良的確沒必要知道何為職業(yè)病防治法了,因為他或許根本熬不過這個春天。法律改了,又能對他有什么影響呢?
作為一名記者,我不知道現(xiàn)在怎樣才能幫助他實現(xiàn)愿望。
當(dāng)我們把目光從郭海良身上轉(zhuǎn)到更多已經(jīng)罹患職業(yè)病或者可能正在遭受職業(yè)危害的勞動者身上時,呼吁修法、快點修法,似乎就成了我們現(xiàn)在所能有的惟一作為。
郭海良的春天還會再來嗎?希望會。我更加希望的,是郭海良們的春天別再遲到。
下一篇:搶救時間考驗工傷法規(guī)